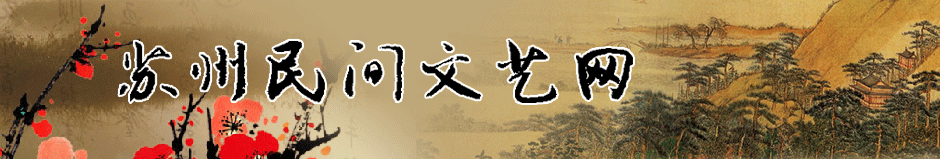“君到姑苏见,人家尽枕河。
古宫闲地少,水港小桥多。”
这是唐代诗人杜荀鹤的两句诗。白居易在《忆江南》中也念念不忘苏州的繁华。千百年来,苏州占全了'天时,地利,人和',并得以充分发挥,被誉为我国的'人间天堂'。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,她所积淀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都是相当可观的。现代旅游业的兴起,四面八方的人们来苏州观光,游园林,过古桥,听寒山寺的钟声。至于吃的、用的、玩的,不但样样都有,而且更是独具特色。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,第六十七回中专门写了薛蟠从苏州买来的两箱子物品,一箱'都是绸缎绫锦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',另一箱'却是些笔、墨、纸、砚,各色笺纸,香袋、香珠、扇子、扇坠、花粉、胭脂等物;外有虎丘带来的自行人,酒令儿,水银罐的打金斗小小子,沙子灯,一出一出的泥人儿的戏,用青纱罩的匣子装着;又有在虎丘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,与薛蟠毫无相差'。可以说,这是三百年前苏州民间手工艺的一个缩影,写的都是几项有代表性的东西。曹雪芹对于民间手工艺是非常熟悉的,也最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。薛蟠买这些东西送给林黛玉,本以为是她家乡的'土物',所谓'物离乡贵',会讨她喜欢,恰恰相反,黛玉见了反自'触物伤',掉下了眼泪。这就是民间手工艺的魅力。
清代道光年间(1821-1850),顾禄出版了专谈'吴趋风土'的《清嘉录》,他以岁时为序,其中也记录了一些苏州的民间手工艺。此书流传很广,版本也很多,连日本也有翻刻本。民俗之所以被重视,是因为关系着大众,所谓'入国问俗'与'入乡随俗',是很有人情味的。有的人评价手工艺过分强调了技艺,实际是一种偏颇。这大概也就是古人所说的'道'与'艺'的关系吧。
在我国,像苏州这样人文厚积的城市为数是不多的。我对她产生浓厚的感情,是在半个世纪之前。20世纪50年代之初,我初到江南,作为民俗和民艺的田野考察,是从苏州和无锡开始的,从中真正体验到了江南的人文之美。对于苏州的民间手工艺,曾经一项一项地记录,约略熟悉其大概。那时候,苏州的手工艺已组织起36个合作社,少者十几人,多者上千人。当时年青,不但了解生产,访问艺人,并且去跑木渎、甪直,到农村看'吴装'。至今还清楚地记得,向朱士杰、顾公硕、顾仲华、徐坛秋诸先生请教,他们都是深谙苏州掌故的前辈,多次谈话使我受益匪浅。我接触过许多老艺人,都是在全国同行业中的佼佼者。如雕刻名家陆涵生,刺绣名家任嘒閒 ,桃花坞木刻的叶金生、许良甫、徐国良,檀香扇烫花的龚福琪,缂丝老人沈金水,泥塑瓜果草虫和通草堆花的阎家兄弟(阎照林、阎照琪),镂刻蓝印花布花版的李广兴等。看他们的手艺和作品,听有关人士的介绍,几乎是异口同声,都是强调手巧艺精;虽然各有千秋,其共同的特点是认真、精致、秀气。俗说'一方水土养一方人',姑苏的秀美也造就了手工艺的高超,形成一种清雅灵秀风格,这就是遐迩闻名的'苏州式'。是那么自然,那么天成,就像'吴娃咿语'一样,带着一种特有的风韵。在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中,'苏州式'不但是上乘的,也是具有代表性的。
民间手工艺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苏州的民间手工艺不仅是苏州人的骄傲,也是全民族值得炫耀的。即使在工业现代化的今天,高科技层出不穷,也无法取代手工之美。手的灵巧不仅创造了精美的工艺品,也演奏出美妙的乐章,描绘出绚丽的图画,以至制造出高科技。在过去,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,手工艺人处在社会的底层,他们的技艺和艺术,自生自灭,无人问津,更无修'志'的可能。现在,经过几十年的积累,上下齐心,从领导到具体的工作者,开展普查,共同编辑了这部《苏州民间手工艺术》,真是可喜可贺。全书翔实地记录了7大类80个品种,有文有图,有史有事,有技有艺,洋洋大观,可谓苏州手工艺的一座丰碑。
历史是不能回转的,但是它所积淀的优秀传统可以延续,就像流水一样流进现代的生活,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。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,也是中华文明得以保持的重要举措。我祝愿苏州的民间手工艺兴旺起来,?quot;苏式'之花盛开。
2005年9月5日于南京梅庵
(本文为《苏州民间手工艺术》序言)
|